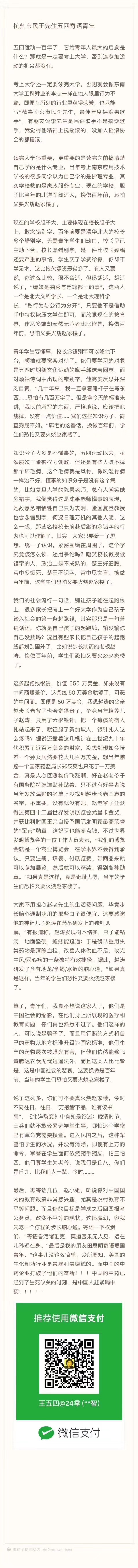“如今我们回来了,你们看便不同了!”
这是1919年的7月,28岁的胡适,在北京“少年中国学会”演讲时的结束语。
胡适说:“这便是少年中国的精神。”
这一年的7月1日,由王光祈、曾琦等人发起的“少年中国学会”,在北京正式成立。学会聚集了一群中国最优秀的青年,他们厌倦了当局,厌倦了现实政治,厌倦了父兄辈的说教,想为泥淖深陷的中国,寻一条新出路。
终身从事社会改良
发起人王光祈,如此解释当日组织“学会”的缘由:
“学会何为而发生乎?有数十青年同志,既慨民族之衰亡,又受时代之影响,知非有一班终身从事社会改革之青年,不足以救吾族,于是不度德、不量力,结为斯会,以‘社会活动’为旗帜,奔走呼号,为天下倡。”
另一位会员李璜的描述,要更为具体一些:
“民国成立之后,军阀主政而卖国也如故,士大夫之肥家养己与醉生梦死也更有甚于昔日。故从‘五四’之前一年又从政治改革转向到了思想改造。”
这些表述,显然深受新文化运动“改造国民性”的影响。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们大多认同“国民程度与国家程度呈正比例关系”这样一个观念。所以,学会当日定下的宗旨就是:
“本科学的精神,为社会的活动,以创造少年中国。”

图:学会创始人王光祈
基于这样的理念,又有鉴于往日旧政治的教训,王光祈们希望学会会员远离现实政治,专心从事社会活动,致力于思想文化的社会传播,以此为理想中的“少年中国”打下根基。
为此,学会制定了这样的会规:
“凡加入‘少中’会友一律不得参加彼时的污浊的政治社会中,不请谒当道,不依附官僚,不利用已成势力,不寄望过去人物;学有所长时,大家相期努力于社会事业,一步一步来创造‘少年中国’。”
在首批会员,南京分会创始人黄仲苏眼中,“少年中国学会”最大的特点是思想自由、言行合一、关注时事:
“‘少中’学会初非一种纲纪严整、规律详密、服从某一领袖、遵守某一主义之集团,而是一种追求光明的运动。会员莫不反对封建主义,祟尚进取,重视新知识,于各种新制度极感兴趣,思想自由,不受约束,所持信仰亦不一致。”
“(会员们)平日务求言行一致,尤以虚伪、敷衍、放纵、标榜诸恶习为戒。聚首时每有辩论,无不面红耳赤,据理力争,事后则又握手言欢,不存芥蒂。”
会员方东美的回忆,与黄仲苏的印象大体无二:
“(学会会员)共计一百有八人,皆个性独特,而思想自由,情感富赡。平居生活抑又律己甚严。吁衡时艰,触发问题,写为文章,先后发行《少年中国》及《少年世界》两种杂志,风声所播,全国掀动。”

图:学会会员方东美
追求个人自由
现实中的国家模样,不是青年们想要的国家模样。
王光祈想要的“少年中国”,是这个样子的:
“理想中的‘少年中国’,就是……要使中国成为未来的大同世界的一部份,使中国人民的风格,制度和学术生活等等都能适合于世界人类进化的潮流。”
具体该怎样做,才能“适合世界人类进化的潮流”呢?
王光祈主张先从改造每个人的生活、追求个人的自由开始:
“我们要创造一个天机活泼的生活,打破形式主义,打破不自然的个人生活”。“这个世界是我们活动的舞台,一切不平等、不自然的束缚,我都要彻底的脱离。”
对个人自由的追求,最终必然会落实到具体的政治体制上来。王光祈研究过当时正风靡欧洲的社会主义,也研究过俄国所推行的列宁主义(1919年的青年,多少都有类似的思想经历)。他很担忧,列宁式的俄国,会出现“国家权力入侵私人生活”的问题:
“该国……采集产制度,国家权力甚大,究竟与个人自由,有无妨碍,实是一个疑问。我极反对机械的个人生活,受这种劳农政府支配的国民,处处都有一种国家权力紧紧跟随,个人生活便成一种机械了。”
出于对现实政治的失望与现实政治势力的警惕,少年中国学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,遵循“不得参加彼时的污浊的政治社会”的会规(会员胡适甚至做出过“二十年内不作政治运动”的承诺),刻意远离政治活动,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社会工作之中。
这些工作包括:教育、出版、新闻以及各种改造个人生活的乌托邦试验;创办了《少年中国》月刊、《少年世界》月刊以及《星期日》周刊,出版“少年中国丛书”30余种;成立“平民教育讲演团”,推行“新村运动”、“工读互助团运动”实践。等等。

图:学会刊物《少年中国》杂志
这种定位,使学会少了许多争权夺利,有一种特别良好的氛围。多年后,学会会员左舜生如此回忆往事:
“在‘少中’最初几年的会员间,实在没有给我留下半点不良的印象。这与我后来所过的党人的生活,和政治上一切勾心斗角的把戏,真是截然不同,而具有充分的人味。”
这种“人味”,也见李璜的回忆。去台后,他回忆起在“少年中国学会”的日子,谈及将自己定为“战犯”的毛泽东时,仍用“会友”二字作为称呼。
而在1919年,王光祈是如此评价这位湘潭青年的:
“此人颇重实践,自称学颜习斋之学主实行”。

图:毛泽东所填写的《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》
一百年前,这名湘潭青年曾尝试在岳麓山建设一个“半耕半读”的新村。
在他的“新村计划”中,学生每天睡眠8小时,游息4小时,自习4小时,教授4小时,工作4小时。他认为,一边读书一边工作的“工读主义”,是一种创造性的新生活;这种新生活,是创造新社会的细胞。他希望新学校里的学生,能够成为创造新家庭的种子;千万个新家庭,“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”。
在他所描绘的“新社会”蓝图里,将会存在公共育儿院、公共蒙养院、公共学校、公共图书馆、公共银行、公共农场、公共工作厂、公共消费社、公共剧院、公共病院、公园、博物馆、自治会……他说,这种新社会,是一种“新村”;“新村”,就是一个个财产公有,共同劳动,平均分配,人人平等,互助友爱的新社会的细胞。
这种理想,显然与王光祈大不相同,甚至相反。
但这也正是“少年中国学会”的可贵之处——思想自由,而非定于一尊。事实上,当时的会员中,“有信仰国家主义的,有信仰社会主义的,有信仰安那其主义的,而且各会员对于他自己所信仰的主义,非常坚决,非常彻底。”
在1919年,这位湘潭青年所寄望的达成上述理想世界的手段,尚不是政治力量,而是社会活动。他在“‘少中’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”中填下了四个字——“教育事业”。

图:1920年7月1日,北京岳云别墅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一周年合影留念
风流云散
但不涉入现实政治、只关注社会改良的会规,终究是难以持久的。
这是一种必然,用会员李璜的话说就是:
“要救国而又不及政治,乃是其中具有言行上的矛盾的”。
社会改良固然有助于推动时代前行,但远没有政治上的改良(革)来得有效;而且,没有政治上的改良(革)作为制度保障,所谓社会改良的成就,也很难固化下来(一如非建制的启蒙难敌建制化的宣传),自然,也很难造就一个新的“少年中国”。
1921年7月,学会成员在南京集会,共到会23名代表。会上,就会员是否应该从事现实政治活动,产生了很大分歧。作为妥协,最后提出一种折中方案——将直接加入政界,定义为狭义政治活动;将从事革命打破现存政治组织,定义为广义政治活动,广义政治活动包含在“社会活动”之中。表决结果,十九人赞成,三人反对。“推翻一切强权政治之革命运动”,成为允许会员参与的“例外”,被写入了会规。
此后,越来越多的会员投入到现实政治活动之中。
1925年,学会停止活动。

图:1921年5月31日,少年中国学会部分会员合影。后排右三为李大钊,右一为邓中夏。
附:学会会员名单
王光祈,周太玄,陈愚生,李大钊,雷宝菁,张尚龄,曾琦,魏嗣銮,赵曾俦,沈懋德,李璜,易家钺,李劼人,雷宝华,宗白华,左舜生,葛沣,黄日葵,袁同礼,罗益增,许德珩,陈宝锷,周炳琳,彭云生,李思纯,穆世清,周光煦,李珩,何鲁之,孙少荆,胡助,易赓甫,康白情,孟寿椿,徐彦之,刘正江,苏甲荣,雷国能,涂开舆,段子燮,陈登恪,赵子章,赵世炎,郑尚廉,黄仲苏,黄忏华,田汉,刘仁静,郑隆瑾,章志,沈君怡,杨德培,朱镜宙,邓中夏,张菘年,陈道衡,赵崇鼎,沈德济,蒋锡昌,阮真,杨贤江,王克仁,谢承训,方东美,王德熙,邰爽秋,恽代英,余家菊,梁空,张闻天,芮学曾,毛泽东,刘国钧,李贵诚,章一民,陈启天,恽震,王崇植,吴保丰,周佛海,张明纲,高君宇,陈政,汤腾汉,杨效春,张涤非,李初黎,杨钟健,沈昌,鄢公复,唐现之,朱自清,常道直,刘拓,卢作孚,金海观,曹守逸,郝坤巽,童启泰,康纪鸿,侯绍裘,杨亮工,须恺,黄公觉,刘云汉,倪文宙,洪奠基,舒新城,苏里乐,吴俊升,张鸿渐,胡鹤龄,任启珊,许应期,浦薛凤,朱公谦,叶瑛,古柏良,程中行,王潜恒,汤元吉。(参考资料:张允侯/等,《五四时期的社团》,吴小龙,《少年中国学会研究》,三联书店。)





 “五四”新文化是我一向重视的一件历史大事,曾先后多次为文讨论。这次百年纪念更激起我对于“五四”的种种反思,其中一部分已见于我和唐小兵教授的访谈录中。但访谈结束后,我感觉还有不少重要的想法当时没有机会说出来。(因为访谈只进行了一小时。)现在我想将其中一些想法组织起来,对“五四”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作用,做一次客观的整体论断。
“五四”新文化是我一向重视的一件历史大事,曾先后多次为文讨论。这次百年纪念更激起我对于“五四”的种种反思,其中一部分已见于我和唐小兵教授的访谈录中。但访谈结束后,我感觉还有不少重要的想法当时没有机会说出来。(因为访谈只进行了一小时。)现在我想将其中一些想法组织起来,对“五四”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作用,做一次客观的整体论断。